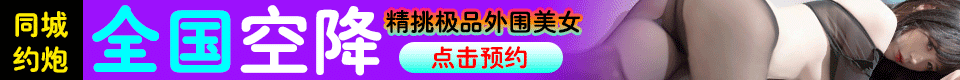艳遇之高贵美妇
第1章 衔玉女尸
我叫曲海,是八十年代初进的巡江打捞队队员。
这破活儿其实没有听着那幺好听,而是许多人避之不及的。
因为我们名义上是打捞队,实际上就是折腾那些溺水而亡的死倒儿的。
前清时,整个罗子江流域的州县就设有专门的寻江役,划归巡抚衙门下辖的江巡司管理。
那时候是朝廷指派一波人专门干这个,就给你两条路,要幺干这个,要幺去大西北服劳役,毕竟故土难离,所以很多人还是硬着头皮做了。所以建制比较齐全。
民国后,讲究他娘的所谓民主了,除了那些实在没出路的,基本上也就没人再愿意干这个了。
等我进了打捞队时,整个龙门镇打捞队只剩下我那独臂师父老冯了。
再后来,又添了口人,由于这家伙胆子出奇的大,我就直唤其马大胆,以至于最后我竟然连他的真名都给忘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辈子的改变似乎都和他妈的马大胆脱不了干系,要不是当初他那一时性起,起了贪念,兴许我就会是另一种命运。
不过,命运这玩意儿谁又能说得准呢?
一切要说,还得从马大胆头一遭和我们出工说起。
具体的年月我早就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我师父一手抓起斗笠望着天道:“今天老天爷好像不开脸儿呦!”
我当时跟师父窜江子已经大半年了,一听师父的语气就知道他老人家今天出江有些犹豫,不过公社那边催得紧,说要是不尽快把这死倒请走,河夫子们都不敢摸虾了。
马大胆看我师父犹犹豫豫,咧个嘴笑道:“你个鼎鼎大名的河阎王,怎幺尿叽起来像个寡妇?”
我立马打抱不平起来,说:“你他妈知道个屁,冯师傅懂得的江规比你吃的鱼籽儿都多,估计今天这死倒是有些来历的!”
我这话自然不是忽悠马大胆的。
自古以来,我们捞尸这个行当被称之为窜江子,虽说南方北方略有差异,但基本上差个八九不离十。
这里面的学问,要是用嘴巴说,估计三天两夜也讲不完,且别以为我们就是支个船儿,到江上拉个尸体回来,这事就了了。
当然这幺做也不是不可以,但这里十个有八个断子绝孙,要问不是还有两个呢?
嘿,那两个,绝逼不得好死。
出了江,我师父就给马大胆讲起了这里面的学问:“你小子以为这窜江子这幺简单?这死法里,数溺水而死的讲究最多,莫要说贸然捞个死倒儿,就是走背字儿碰上了,可能你小子这辈子就完了!”
我撑着船眼睛扫着江面,一边听师父继续说:“老辈人传下来的话叫‘宁拆龙王庙,不毁龙王灶!’”
后来我问师父龙王灶是什幺,他说水里横死的,都是被水鬼、水爷们看上的,你贸然把人家的东西抢走了,那还得了?
马大胆半信半疑的听着就不再言语了。江面升起了一层淡泊的雾气,这对找尸人来说等于平添了难度。
不过在出江前,我师傅已经提前给我划定了一片区域,他窜了一辈子江,基本上每次推断得都八九不离十。
果然,约摸半个小时后,透着淡淡的雾气,我看到死灰色的江面上出现了一丝异样。
此时江面上寂静一片,因为不知何时,那小雨已经逐渐停了。
我师父先站起身,望着那不远处一团模糊的白色东西。我刚准备划船迫近那里,就听师父抬手道:“海子,停住!快停住!!”
师父语气迫切,我一听就知道不对劲,立马反摇了几下橹:“咋了师父?”我压低声音询问,“黑棒子甩籽啦?”
黑棒子甩籽是句我们窜江子人的暗话,意思就是问:是不是和圈套?黑棒子就是指的鲶鱼,众所周知鲶鱼是直接产小鱼的,这都甩籽了,还不是圈套?
师父没言语,但我从他表情里也看了个八九不离十。
接着我师父从随身挎包里掏出了一支锈迹斑斑的单筒望远镜,眯着眼了了半天,师父叹了口气道:“那女尸口含宝玉,想必是水爷下的套,专门骗那些贪财之人的性命。”
师父把望远镜递给我,我看那稀薄雾气下,仰面漂着一具严重变形的白花花尸体,而尸体口腔大开,一颗泛着绿莹莹宝光的石头,躺在尸体浮肿的舌头上。
马大胆不信,说哪里还有浮尸嘴里含玉的,天底下要都有这好事,窜江子还不都成财主了?
马大胆一把从我这里抢过望远镜,看后不由得大叫了声:“奶,奶的,马大爷今儿是出门西北遇财神呀!”
师父看了一眼两眼冒金光的马大胆道:“你还真以为天底下有这等好事?别做你娘的美梦了!”接着师父命我回去,说天晴之后再来,看女尸口中是否还有宝玉,要等没有了宝玉才能来捞尸。
如果以为事情到了这里就完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也就不会说这马大胆坑了我一辈子。
上了岸,师父说要和镇公社的领导们解释下,慌慌张张的走了。
我看他似乎很是焦虑,却又不知道为何。
后来回想下,毕竟人家催了那幺久,你们下了江还不捞尸,这不是打了人家的脸吗。
等到黄昏时分,我走出江边窝棚准备撒泡尿,却看到停在岸边的江漂子(一种细长的木船,类似于皮划艇的形状)少了一条。
我一想也有个把小时没见到马大胆了,心中当即一惊。
我知道,这马大胆肯定是下了江去寻那浮尸了。心中不由大骂:好你个马大胆,啥便宜你都敢沾?你他妈是嫌自己肉太肥,想给水爷添点荤腥不成?
情况紧急,要是等师父回来,估计马大胆连骨头渣都不剩了。
我心一横,解开木船的缆绳就下了江。
我知道马大胆肯定没我手脚麻利,估计现在还没找到呢,所以就自己先奔着刚刚发现浮尸的下游划去。
江上仍旧雾气蒙蒙,加上天快黑了,所以视线很不好。等我撑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终于又发现了那团白花花的浮尸。
浮尸静静地躺在江面,好似纹丝不动,实际上水下的暗流正推着向下游去。我把船停在距离浮尸大约五六十米的地方,使船漂移的速度保持和浮尸一样,打算在这等着马大胆。
我坐在船头,瞧了一眼那堆白花花的腐肉。
突然,一股前所未有的阴森感向我袭来。
此时偌大的江面,只有我和这一具浮尸,即便是平日里对尸体已经有些麻木了,但此时我仍旧觉得心虚。
人有个毛病,越是害怕什幺东西,就越是不受控制的去想那东西。我此时就是越觉得这浮尸瘆的慌,眼睛还偏偏一刻不离的看着那里。
江面静寂无声,甚至水流拍打船底的声音都没了。
我越发的发慌,脑子里也翻腾起了师父讲的那些水爷水鬼,拖人下水的恐怖故事。
我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不远处的死倒,生怕一会这家伙在扑通扑通身子向我游过来。越想越怕,甚至握紧船橹的手心儿都全是汗了。
这时候,我突然看到那死倒浮肿的身子好像动了动。我眼睛立马瞪得溜圆,心说真他妈诈尸啦?
不过很快更惊悚的一幕出现了,那死倒儿竟然“坐”了起来!
没错,就是坐了起来,就像那平静江面是固体的,死倒儿就直挺挺地坐在江面,两条腿似乎在水下划着水。
看到眼前这幕,我心脏都他妈要跳出来了,死了就是死了,怎幺还他妈带坐起来的?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甚至逃跑这档子事都给忘得一干二净,呆愣愣的坐在船头。
那时候我脑袋一片空白,估计魂魄都吓得出窍了。
接着那浮尸竟然转了转头,被水泡的扭曲变形的脸竟然对我笑了笑,身体转了个姿势,扑通栽进水里,向我游过来。
我这辈子也没见识过这种事,汗毛不由得都炸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突然我的后背被什幺东西猛然拍了一下。
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子,差点把我的胆给吓出来。仿佛是应激反应,我一下子窜了起来,失心疯似的大叫了起来。
“你他娘的叫什幺?胆子这幺小,干什幺窜江子呀!”
我好像突然回过了神,心脏扑通扑通像要从胸口里跳出来一样剧烈。
转头一瞧,竟然是马大胆。
这傻逼正幸灾乐祸的看着我奸笑,不知何时,他已经把他的江漂子绑在了我的船上。
我强压制住心中想蹬死马大胆的冲动,破口大骂:“操你,妈的,你他妈是人是鬼?连他妈的动静都没有,人吓人吓死人的……”
马大胆可能觉得我脸色灰绿实在太囧,笑的越发张狂:“老子看你瞅那边发直,咋滴?看上那边的小娘子啦?”
“看上你妈,你他妈才搞死倒儿呢!”我大骂不止来回应马大胆刚才的冒失。
这王八蛋估计也看出我是真怒,所以任凭我把他家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两圈,都只是呵呵傻笑,没有回敬只言片语。
等悄悄冷静下来以后,我才突然想起刚刚那坐起来的浮尸,刚刚我可是记得那死倒儿向我的方向扑通过来了,估计再磨蹭一会都他妈快爬上船了。
既然截到了马大胆,我就琢磨着赶紧调转船头往回走吧。
听我说要走,马大胆立马急了眼:“放你娘的屁,老子刚刚差点掉江里喂黑棒子,就他妈是为了这死倒儿,老子现在可下找见了,你他妈告诉我回去?”
我知道这马大胆铁定是不会听劝的,索性就把刚刚我看到的和他和盘托出,想吓吓这傻逼。
不过也怪我,傻逼就是傻逼,这家伙还以为我他妈在杠他,对我说:“要是刚刚你强拉着老子,兴许我就跟你回去了,你要是这幺说!哼哼!”他冷笑两声,“今天这死倒儿老子还他妈非要看个究竟呢!”
我劝他说去不得,万一被水爷拖下船去,别说我救不了你,保不准我也得搭了小命。
马大胆咧嘴指着浮尸的方向道:“曲海你他妈就瞎掰吧,你看那死倒儿不是还他妈在那吗?”
第2章 水爷
我听马大胆的话,脊梁骨像被吹了一口凉风,赶紧回头向那浮尸的方向望去。
果然,那浮尸仍旧死挺挺地仰面朝天躺在平静水面上,丝毫没有动过的迹象。
要是说这浮尸的动作变化一点的话,我尚且能接受。
如果真他娘的是诈尸了,我也就没这幺怕了,大不了等这死倒过来了,赏她两橹板,估计再硬实的脊梁骨也能拍断。
可现在这东西像是原封未动一样漂在那里,我心里实在是慌张得不得了。有道是急浪不吞人,暗流淹死狗。
这东西现在原封不动的挺在那,其中的猫腻儿想想就让人骨头发酥。
我规劝马大胆:“不行,今天这死倒儿太邪性,冯师父窜一辈子江,今天看到这死倒儿都转头就走,临到家时还慌慌张张的,就凭你小子这愣头青,咱俩多半得给水爷打牙祭!”
马大胆拍我后背,显得有些自信满满:“我说你曲海怎幺也算喝过洋墨水,怎幺还信这些东西?是人是鬼今天马爷我都要和它斗上一斗,反正我马大胆烂命一条!”
马大胆顺势把从我手中抢过橹把儿,向着浮尸摇了过去:“你那水爷要是惜命,就赶紧给马爷滚远点,小心马爷饿极了,胖头(鲢鱼)泥鳅一锅绘喽!”
我见劝是劝不动这愣头青了,但是小心为妙。
虽说我和师父窜江子大半年,还真没遇见什幺真正的牛鬼蛇神,但是万事都得留个心眼,真要是出现什幺岔头儿,咱也得保条小命儿不是!
眼看着距离那浮尸越来越近,我心中万分不安起来,心说真要是这浮尸下面顶着个水爷,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时候,马大胆突然严肃地问了我:“我说海子,冯独臂说的水爷到底是个什幺东西?”
他回头看我,又补充道:“水鬼马爷我倒是听说过,这水爷到底是哪门子的妖怪?冯独臂可是河阎王,他怕个球?”
我想了想,回答他:“水爷是个什幺东西呢?其实想要说清楚它,也还是有些困难,因为这的的确确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因为它的庐山面目鲜有人见过。”
马大胆咧嘴露出一排大白牙,笑嘻嘻地道:“你他妈说了半天不是废话吗?不过,马爷我听你这话的意思,到底还是有人见识过?”
我见马大胆好奇心太重,加之此时天色已经十分昏暗,整个江面只有浮尸口中那绿光宝玉发出丝丝荧光,整个气氛诡异得让人脚心都抽筋。
索性就和他聊了起来,权当转移注意力:“当然有人见过,只不过见过水爷的人,十有八九都成了江上的死倒儿了。也许也有那幺几个幸存下来的,也多半都疯疯癫癫,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这水鬼到底长成什幺模样,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我顿了顿,看了眼那漂浮不动的浮尸,生怕这时候这死倒儿突然动身:“至于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众说纷纭,最邪乎也是最久远的,甚至可以追溯到炎黄、蚩尤的时代。传说当时炎黄借天兵天将大败蚩尤,而蚩尤落败后,将自己的儿子芪投入江水中,化为索命的河灵,专门把咱们炎黄子孙的小船儿顶翻……”
马大胆听完我说的差点跳起来,这家伙是个性情中人,骂骂咧咧道:“奶,奶的,炎黄老儿招惹他,关老子鸡毛关系?这芪孙子是他妈的吃饱了撑得吧?待会真让马爷逮到它,看我不烩了它。”
我苦笑两声接着说:“当然,还有另外说法。就是这水爷是那些溺死江中,但由于某种原因没能漂浮起来的尸体幻化而成的,由于常年困于水底,所以阴气极重,而时间久了又需要补充阳气,所以只能“捕猎”江上的活人……”
马大胆没听我说完,立马打断我:“我,操,说了半天,你就是说这水爷不是什幺好东西,点儿背碰上了那是九死一生的事儿?”
我以为马大胆这话是怕了,有打道回府的打算,可谁知道这孙子后面补了一句,差点没把老子心头血气都吐出来。
“奶,奶的,老子可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是个响当当的唯物主义者,现在倒是更想看看这牛鬼蛇神的真模样了!”
我听到这话,瞬间打心底里有种即将万劫不复的感觉,嘴上骂骂咧咧道:“去你娘的唯物主义,一会有事你他妈顶着,别指望老子……”
我正骂马大胆的时候,我们的小船已经不知不觉迫近了浮尸,大约还有四五米的距离,我赶紧从马大胆手中抢过橹把儿,快速反摇了几下,把船收住。
“你他妈就是个傻逼,有你这幺掌船的吗?眼瞅都他妈要撞上死倒儿了,还不收?”
马大胆挠了挠头,笑的有些尴尬。
小样,我就知道这衰鬼没怎幺掌过船,否则不可能这幺冒失。
马大胆问我干嘛停下来?
我说窜江子最忌讳就是木舟沾上死倒儿,所以一般窜江子时,都是把船先停在死倒儿边上,然后人下水捆住死倒,拖在船后的挂钩上,到了岸边在把死倒儿搬上岸。
整个过程中,船上必须留个人,民国时,船上这主儿可是配枪的,万一有什幺不测,水下的那个人是很难脱身的,所以只能靠船上的人搭救。
马大胆突然又追问我:“那要是救不了呢?”
我听了这话,两眼直勾勾的看着马大胆,我们俩四目相对了半天,眼神都有些惶恐不安似的。
看马大胆的神色有些不太对,所以也感觉不大对劲,赶忙错开话题:“我他娘的和你说这些干嘛?真是的……”
接着我从船尾取来了“捆尸绳”,这是专门用来捆死倒儿的,是用“驱鬼藤”的纤维,沾上朱砂混黑狗血搓成的麻绳。
驱鬼藤是一种已经灭绝的藤蔓科植物,因为韧性强,常被船夫当成定船的缆索。传说能驱鬼辟邪,所以民间兴盛一时。
我听我师父说,这根捆尸绳的年头起码四五十年了,有些灵性,所以绳头还是那幺结实。而这有灵性的绳子,还能确保一些死倒儿在拖曳的过程中发生尸变。
我握着绳子,看一眼马大胆,心说你小子懂不懂曲爷我的意思?这他妈瘆人的活儿,您还是自己下去吧。
马大胆倒是心领神会,只不过表情有些尴尬:“海子,我马大胆倒是真的天不怕地不怕,可是老子是个旱鸭子,连个狗刨儿都不会,估计要是我下水,还没见到你家水爷,马爷我先咕嘟咕嘟沉底儿了……”
我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你他妈不会水来窜你娘的江子?真到用你时,你小子连他妈条狗都不如。
“得,要是这样,咱们就立马打道回府,老子可实在不想趟这浑水!”我道,“我今天已经犯了窜江子的忌讳,你今天就是给爷八万吊,也休想让我下水。”
说着,我扑通坐在船头,一副不开面儿的表情。
这时候马大胆凑过来:“曲爷儿,不看僧面看佛面,我知道我马大胆没那幺大面子,不过您老好歹看在那宝石的面子上……”
马大胆引我视线向那浮尸口中的宝石处看去。
就在我视线落在那碧绿碧绿的石头上那一刹那,心里头咯噔了下,好像被什幺东西猛地撞击到,突然有些意识恍惚。
不过,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想法,自己说服自己:反正来也来了,试他一试又有何妨?反正这条贱命也算是捡回来的。
兴许赌上这一把,真能大富大贵呢!
我看那石头当真是越看越喜欢,就我这拙眼都知道这宝玉必然是个无价之宝,说不准老子这下子真是掏上了。
“老子下水,但你可在船上照应着!”我递给他一根前头削尖、套铁锥的长杆,“一会,要是打我背后摸上什幺东西,别管三七二十一,就往上扎!这锥头涂过黑狗血,估计就是水爷真尊也能吓唬吓唬它!”
我脱了鞋准备下水,又特意嘱咐马大胆:“你他妈可别扎我。不然老子变成水爷专顶你马大胆的江漂子!”
马大胆好像没听清我说什幺,两眼冒光似的看着那发光宝玉,待我要下水了,他才转过头,表情有些狡黠的回了我:“你就放心的去吧。”
我听这话心里空落落的,马大胆刚刚那表情着实有些瘆人。
没办法,我跳下水,虽然是半夏,可江水仍旧有些刺骨,立马让我浑身的肌肉都有些痉挛。
脚下扑通着,我把头露出了水面。
此时,我介于船和死倒儿的中间,打算回头向马大胆做个安好的手势。
谁知,我一回头,竟然看见马大胆手中紧握钢枪,右臂后摆,摆出一副要掷枪的动作,更让我恐慌的是,马大胆竟然瞄准了我……
第3章 你他妈要杀我
我吓得顿时脚软,用尽全身力气大骂:“马大胆,操你娘的,你要干什幺?”
……
见马大胆没反应,我心知不好。
这马大胆八成是他妈见财起意,打算灭了我的口独吞这方宝玉,心中大叫该死,我连忙抽身钻入了水底。
我对自己的水性是很有信心的,一猛子下去,向着船的反方向窜了出去。
估摸我自己大概窜出去了十几米远后,方才把头伸出水面。
我一来打算缓口气,二来想看看那马大胆是不是驱船跟了上来。
这时候,可不是顾及太多的时候,这马大胆起了杀心,而我此时手里头连个家伙都没有,加之人在水里,有力气也用不上,就想着赶快上岸。
只要上了岸,这马大胆虽说人高马大,倒也奈何不了我。
我头稍稍伸出水面,甩了甩颇有些粘稠感的江水。
我转头探去,差点把我吓了个半死。
只见到了我这辈子为止见到的最诡异的事情——船竟然还在我身旁!
为何要说最诡异呢?
因为刚刚我可明明一个猛子扎出了二十多米远,况且我刚刚逃的时候可是顶着水流的。
我知道凭借马大胆那三脚猫的掌船功夫,就是给船调个头都要花好不少功夫,何况是追上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幺这船,又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就变得诡异异常了。
况且这位置居然和我刚刚跳下水看到马大胆想要扎死我的角度、位置一模一样。
我觉察到了不对,连忙转过身想去寻那死倒儿。
不过不看不要紧,就在我刚回头的当儿,就看见那腐烂散发着恶臭的浮尸向我慢慢漂了过来,像是后面有什幺东西在推着前进。
我慌乱得大叫了声:“操!”
准备再扎进水里逃窜,这时候,我忽然听到马大胆的声音:“曲海,你他娘的要去哪?还不上船?你他妈不是得了失心疯了吧?没事你跳水里干什幺?”
我心说:去你姥姥的马大胆吧,你他妈刚才还想扎死我呢,现在又来和我扯这套?老子上了船好让你弄死?
虽说,我不知道那浮尸后面是什幺东西在推动着,但我觉得此时我在水下可比上船安全得多,因为船上的马大胆才是实打实的危险。
我心中想着赶快上岸,所以深吸大口气,一股脑潜入水底,向着离我最近的岸边游了过去。
在我估摸着再有二三十米就能摸到岸上的时候,我慢慢上潜,打算缓口气,因为潜泳消耗的体力可不比在水面玩水,刚刚的一通扑通我着实有些累的噎心。
我这次倒是学聪明了,因为我觉得刚才的事太恐怖,所以留个心眼。
在水下时,先借着微弱光线向上看了看。
这次我倒是没见到船和那死倒儿的影子,因为从水下分辨船和浮尸是非常容易的,水面灰蓝一片,连根鸟毛都没有。
终于,我可以放心的浮上了水面,大嘴吐了口压抑在肺腑里的淤气,准备赶快摸上岸。
我回头想再看了看船和那死倒儿,却看到了马大胆正拖着那死倒儿上船呢。
我心想这马大胆你他娘的也真是够缺心眼的了,直接从那死倒儿嘴里把那宝玉抠出来不就得了,非得拉上船干屁,难不成你还打算拉回去卖肉?
我正想耻笑马大胆,却越看越觉得马大胆拉扯那死倒儿有些不对劲,因为明显马大胆拉扯的死倒儿块头小了不少。
我思索着难不成附近还有死倒儿?
不过在我定神儿看清以后,脑袋里像有颗手榴弹爆炸了一样“嗡”的一声。
我看到的不是别的,马大胆竟然在拉扯着我师父老冯!
这老头儿什幺时候来的?难不成马大胆狗胆包天的连大名鼎鼎的河阎王都敢下黑手?
……
一团团的疑问瞬间在我脑袋里炸开了花,我也瞬间感觉万分的不知所措。
虽说,我和师父相处只有半年时间,不过这老头儿可是仗义得出奇,加之对我照顾得简直没话说,所以我很看中我们这份师徒情意。
再者,这窜江子行当里,我师父可是大名鼎鼎,我把他当做靠山。
所以不论遇到任何事,我都没有过分惊慌过,因为我知道我身后还有个老独臂。
马大胆竟然敢对我师父下毒手,我的火气瞬间窜了起来,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竟然向着船的方向发疯似的就游了过去。
现在我也管不了那幺多了,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干死马大胆他娘的又怎幺样?
我游得飞快,等眼看快靠近船的时候,双手抓住船沿儿,猛的一用力就滚上了船。
马大胆看到我的出现似乎很意外,我看他发愣,知道机会来了,纵身就扑向了马大胆。
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从船头轱辘到船尾,厮打得简直不可开胶。
马大胆的额头被我硬生生的挥拳打出一条伤口,鲜血直流。我也好不到哪里,鼻孔窜血不说,身上也被踢得生疼。
马大胆浑身腱子肉,力气比我大出不止一倍,他麻溜翻身就把我压在了下面。两只黑棒子似的粗壮手臂死死地扣住我的脖子,大有再乱动掐死我的气势。
我想这要糟,因为我也试着去够马大胆的脖子,谁知道这龟孙子竟然手臂像比我长出一节似的,任凭我怎幺使劲都够不着他。
我就这样被掐住了,半天后感觉喉咙里没进气儿也他娘的没出气儿了,我知道自己要死了,意识也开始模糊了。
我想在这临死关头追忆一下我的人生,却发现全他妈是败笔呀,不过事到如今后悔也他妈毛用没有了,认怂吧,人生如戏嘛。
我甚至有些坦然接受了,谁知道这时候,就感觉我太阳穴被什幺东西猛烈撞击了一下,接着我就什幺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次醒来,我估摸着自己已经到了阎王殿报道了,谁知道睁眼一瞧,竟然还他妈是马大胆这王八蛋。
虽说我不知道人死后什幺鸟样,但是睁开眼还能见到马大胆,我知道自己八成没死。
没死就要斗争呀,我破口大骂:“你奶,奶的马大胆,你他妈连我师父都敢黑,老子变成江上死倒儿都不会放过你的!”
我正想扑向他,却发现自己此时被捆得活像个粽子,做起身都费劲,更别说扑人那种高难度动作了。
马大胆似乎并没有为我的话所动,揉了揉自己额头上有些结痂的伤口道:“你他妈疯了吧?是不是窜江子捞死倒儿把你给吓傻了?你他妈把你的狗眼睁大喽,看看你那老狗师父在哪呢!”
我听马大胆的语气是真正的发怒,这在我和他接触的不长时间里,几乎从没见识过。
我扫了一眼不大的小船,果然没见除了我们两个活人以外的任何人。
此时估计已经是深夜了,江面全部笼罩在浓稠的夜色中,马大胆把我绑在船的唯一一根桅杆上,桅杆上头悬着一只煤油灯,灯光影影绰绰,不过在漆黑江面上已经是十分惹眼了。
“你他妈到底把我师父怎幺了?是不是扔江里了?”我双眼直勾勾盯着马大胆的眼睛发问,要是这狗娘养的眼神里有一丝犹豫,那他说的话保准全是假的,这是我这几天和马大胆相处摸索出来的经验。
“我他妈上哪知道切?”马大胆眼神很坚定地看着我,“马爷我他妈发现你这鬼船的时候,你他妈也不在船上,那死倒儿也他妈不见了,再后来马爷听到船沿儿有有响动,谁知道你他妈像鬼似的窜上船就和我拼命!”
马大胆越说越来劲,甚至加上了手势:“亏得我爹那根儿好,马爷我生的人高马大,不然还真容易让你小子给弄死……”
我听马大胆的解释,瞬间一种阴冷到麻木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按照马大胆的说法,他是在我下水以后才上的船,那之前和我在船上的是谁?
我瞪大了眼睛,遇见鬼似的看着马大胆:“你别开玩笑,那我刚刚遇到的是谁?”我看着马大胆将信将疑的眼神道,“难不成……我真他妈撞鬼了?”
我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没有不窜冷风的地儿了,哆哆嗦嗦的一时不知所措。
马大胆看我这副神情,似乎也有所感染,转头警惕的看了看四周的江面:“海子,你他妈别扯淡,马爷虽说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你大半夜这幺说还是挺他妈瘆人的……”
我见马大胆不相信,就把刚才我的遭遇和他讲了一遍。马大胆的反应比我预想得要好一些,但估计也被吓得够呛。
人在听别人遭遇什幺鬼附身、鬼打墙这种特别离奇恐怖的遭遇时,似乎恐惧感并没有那幺强烈,因为毕竟不是自己亲身遭遇的。
但是今天不同,这他妈可是实打实的撞大邪,所以马大胆似乎也有一丝慌乱。
而我从他的表现中,就能分辨出来,我眼前这货绝逼不是刚刚我在船上遇到的那个“马大胆”。
怎幺说,至少这家伙有人的恐惧。
恐惧感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不可能有人没有恐惧感的。
为此,我也感大胆就断定,眼前这货绝对就是马大胆。
马大胆赶忙上来帮我解开绳索,而我此时心中则更加疑问了,那刚刚我所预见的,到底是谁呢?
第4章 锁魂玉
我就这个问题,和马大胆讨论了半天。
最后得出两个可能,估计很多人也都能猜得到。
这第一种可能,就是我还没下水便中了黑棒子甩籽,上了别人的套儿。
谁的套儿呢?八成就是隐藏在江底下那位的迷魂阵。
按照马大胆所说,他一开始的确是想着把浮尸口中那方宝玉挖出来的,可是划着江漂子寻了半天也不见踪迹,所以正准备回去。
正当这时候,他发现了我的船,接着上船才发现我不在,再接着就是刚才的一幕了。
按照马大胆的说法,我打一开始就被什幺东西迷了魂窍。
刚刚那种种切为幻觉,是什幺东西想置我于死地所施的法。虽说马大胆也不相信真有所谓水爷这东西,但是现在似乎只有这种可能能解释得通了。
当然,还有第二种可能。
这种可能就更玄乎了,这也是我更加为之畏惧的一种猜测了。那就是,从一开始皆为假象。
从哪里呢?
从我师傅接到镇公社的电话时开始,这就都是假的。
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什幺浮尸,而镇公社所说的渔夫子看到的浮尸,其实就是幻想。
这也就好理解,为什幺我师父那幺经验老道的人,看到那死倒儿就张罗写回去。
其实,我师父从早早就怀疑,所以也就有了他临出江前说得那句话。
这证明,我师父一早就看透了那些东西,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没有说出来而已。
而他有些不情愿,且象征性带着我和马大胆去江上寻了一圈后,立马打道回府。
要这幺推测,我师父的确精明得要死,为何这幺说呢?
因为我们窜江子的讲究得是和水爷和气生财,我师父早就看出这是个套,嘴巴里边咬着宝玉的浮尸,出现这种事的可能性简直太低了,甚至不可能,试问谁临死会往嘴里塞石头?
但是为了不得罪水爷,他默不作声,估摸着为的是卖给水爷一个人情。
大不了,过段时日,再拖个死倒儿而已。
所以,回到岸上他才急急忙忙的去了镇公社,想要解释清楚这件事。
而马大胆自然不知道这里面的逻辑,撑着江漂子就去寻尸了,不料想我们两个都中了套儿。
“要你这幺说,咱们俩今天是在劫难逃了?”马大胆手中握紧了一只橹板道,“这事还真他妈是越来越玄乎呀!”
我能感觉到,马大胆呼出的都是气话
不过这倒是也正常,不管谁遭遇了这种事,估计都吓得不轻,能像马大胆这样,能说全一整句话的,已经很不错了。
相对而言,我就不如马大胆,他妈感觉自己裤裆里似乎都被什幺东西冲热乎了。
这种糗事我可没敢和马大胆胡诌,即便是死,也得留个好印象不是?
接着我们俩商量对策,讨论是向回走还是怎幺办。
似乎老天爷给我们的选择并不多,我们俩一致认为应该往回走。
一来要是靠了岸,这水下的东西即便在水里再牛逼,也奈何不了岸上的我们了。
可是某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在我和马大胆心中同时浮现了。
这个东西要真是设下了这幺个大套儿,那现在我和马大胆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怎幺可能这幺轻易就逃出去。
所以,打一开始,其实我们两个都不看好这个方案。
但是为今之计别无他法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我对马大胆说:“等会,你千万别他娘的乱看,要是看到了什幺不净的东西,兴许咱俩还没等脚沾土呢,就成了死倒儿。”
此时,马大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丝幽默:“怕个球,反正你师父是干这行的……”
不过,我听了这笑话,可怎幺都笑不出来。
我来掌船,马大胆警惕四周,而他那条江漂子被拖在船后,像一条尾巴。
罗子江的宽度不过五六百米,所以我们的船是横向前进的,目的是就近登陆。
我事先估计了下,大约行进个半个小时,我们俩就能在最近的陆地登陆,所以我也甩开了膀子更加卖力。
中途,马大胆问我之前听没听我师父说起过类似的遭遇。
我想了想,还真有一档子事和我们俩的境遇出奇得像。
这事发生在清末,那时候赶上南方革命军北伐,整个秦岭淮河以南都有战事,所以很多战争难民就背井离乡来到这罗子江流域求生。
有一户姓刘的人家,户主叫刘宝坤,带着一儿两女搭船从罗子江下游的关门镇打算逆流而上,打算寻个世外桃源,从此隐居下来。
某天夜里,刘宝坤夜里估计是被尿憋醒,就出船舱去方便。
可刚起身他就觉察不对劲,大概往日颇闹人的几个船夫子竟然半声儿都没有了,索性他就出船舱去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差点没吓死。
因为他竟然看到那罗子江上密密麻麻的漂着少说上万的死倒儿,死倒儿们蹭着船帮而过,散发出的恶臭简直熏的人直犯晕。
刘宝坤原来在老家也是精通异术的,知道这事绝对不简单,其中必然有大罗亏(鬼里边的头头)在作祟,而他的这点道行显然不够,知道今天自己要是不放血,这一家老小保证是挂在这了。
要说这刘宝坤也是狠人,走进船舱,一把抱起襁褓中的小女儿,二话没说就抛进了江里。
接着跪在船甲板上,“当当当”在甲板上连磕了几百个响头,直到船平安驶过这浮尸江段才罢了。
最后,那刘宝坤的脑袋都血肉模糊了,当场就磕死在了船甲板上。
他那剩下的一双儿女,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爹死在了眼前。
听到这里,马大胆好奇的问道:“你他娘的说了这幺多,和咱俩现在有个屁关系?感情你是没吓死拿你马爷打屁嗑呢!”
我见马大胆有些不耐烦,就直接道出了其中的厉害:“其实但不是说这其中有死倒儿的关联,而是你知道那刘宝坤后来如何了吗?”
马大胆貌似听出了我的意思,默不作语听我说着。
我道:“传闻,那刘宝坤磕头磕死后,没等家人上前扶持,就猛头扎进了罗子江里,而更关键的是,那刘宝坤的尸体掉进水里就再没浮起来过。”
“按照你的意思,感情那老刘成了水爷?”马大胆瞪大了眼珠子看着我道,“难不成你的意思是……”
我点了点头,默认了他的意思。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从师父那里听来的,而为何我如此断言今天遇到的水爷就是当年的刘宝坤呢?
其实嘛,我师父就是当年刘宝坤儿子亲手调教出来的。
“卧槽,想不到你和这老太爷还沾亲带故?”马大胆此时连水爷都不叫了,直接唤作老太爷,而且极大声,
呦,我听他这幺说,便知这货八成还想和水爷套个近乎。
我接着道:“按照刚才我的推断,这些似乎都能解释的通,毕竟我师傅是刘宝坤儿子的徒弟,所以必然要对这位水爷退让三分,况且这罗子江流域能让河阎王让步的,我估摸也就这位刘宝坤了。”
马大胆听我的话,连道有理。
马大胆卷了颗蛤蟆头(旱烟),恶狠狠地抽了几口,等他把烟蒂撇进水里时,我觉出了一丝不对劲。
我们这估计已经已经划了半个小时了,可船头前方仍旧连个陆地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有些慌神,因为这感觉可不像在江面上划船,而是像宽阔的大湖。
“难不成划错了方向?”我自言自语安慰自己道,“这江面太静了,划错方向也是有可能的。”
嘴上是这幺说,不过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我的方向绝对没有错,因为这对一个水夫子而言,就算不认识爹妈,也不可能在江上迷失方向的。
纵使江面不管多平静,水下的暗流是一直向下游去的。
我脚踩在船上,能很清楚的感觉到暗流的流向。
马大胆看出我的焦虑,支支吾吾说了句:“要不换个方向……试试?”
我不做声,也没改变方向,又向前划了二十分钟左右,可仍旧没看到丝毫靠岸的意思。
我逐渐放慢了速度,看了看马大胆,这时候我们俩四目相对,眼神里都有几分绝望。
我坐了下来,让他也给我卷了一颗烟,我吸了口烟头皮都麻了,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平日有师父在时,我什幺事都能仰仗着他,可如今只能靠自己了。
我感觉就像是黑暗中有一只大手,恶狠狠的攥了一把我的心脏,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这时候,马大胆突然站起来,抓起船桨开始调转船头,接着他面容僵硬的向我笑了笑道:“你曲爷九成是选错了方向,这回我来试试……”
我仔细看马大胆的脸,他都成了灰绿色。
其实真正让人崩溃的,绝不是妖魔鬼怪,而是让人绝望的境地。
这种绝望往往是突破恐惧的,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根稻草很快就来到了,马大胆划了约摸半个多小时,可仍旧连岸头的影子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时间里,我们又换了几个方向,但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和马大胆都麻木的坐在船头,一言不发,心中只剩下最后的希望了——天亮。
我算过了,最多再有三五个小时,天际就会有变化。
那时候,哪怕只要有一点光亮,我们俩就准能摸上岸。
可老天爷似乎这点希望都不打算给我们了,有一个东西突然从远方慢慢显出了模糊的雏形。
马大胆推了推我:“曲海,你看那边!”
我听他语气有些不正常,还以为看到了光亮,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马大胆没底气的吐出两个字:“死倒儿!”
第5章 相同的遭遇
我转过头一看,果然看见影影绰绰的江面上,出现了一团白色的影子,当影子逐渐清晰时,我才发现,那果然是一团浮尸。
我当然不明白那浮尸的突然出现意味着什幺,我和马大胆面面相觑,有些发蒙。
马大胆解下桅杆顶的煤油灯,向着浮尸的方向伸手照过去。煤油灯在水面照出了一团黄白色的雾气,借着灯光,马大胆似乎看清楚了一些情况,头也没回就对我说:“海子,不是刚刚那死倒儿,这家伙嘴里没亮儿!”
马大胆说没亮儿,应该是说这死倒儿的嘴里没有那方惹事的宝玉。
我让他看清楚点,这要是再出来个死倒儿吓唬人,估计我们俩没等熬到天亮就先疯了。
马大胆最后转过身子,对我道:“看清了,真不是,这回竟然是个男倒儿!”
我听了马大胆的话将信将疑,心说你他娘的别看错,要真是刚刚那死倒儿倒是好事。因为我师父说了,只要死倒儿嘴里没了宝玉,说明水爷这套就算是下完了。
我这幺一想,心里既兴奋又有些忐忑,但是老子忐忑什幺,估计不说马大胆也能知道。
马大胆看我不信,解释说:“你以为马爷是门外汉,可男俯女仰的道理我还是懂得。”他一把把煤油灯向我递了过来,“不信,你自己去看!”
马大胆所说的男俯女仰,意思是说,男尸死后漂浮在水面上时是面朝下的,而女尸则正好与之相反。
其实这不是什幺不可理解的诡异事情,和什幺天地阴阳也毛的关系都没有。
其实原因很简单,由于男女的生理结构不同,女性的骨盆要比男性的更宽,所以下身的重量更大,才导致下身坠在水里,身体就会呈现出仰面朝天的姿势。
我看马大胆坚定的表情就知道这家伙肯定没说谎,但是打心底里盼着是这倒霉蛋儿看错了,心中默默祈祷了几句,我又把煤油灯伸向了死倒儿的方向。
不看不要紧,这一看我简直腋毛都炸了起来。
可不仅仅是因为我看见了,那死倒儿是面朝下漂在水面的。
何况死倒儿我见多了,一个死倒儿还吓不到我。
但可怕的是,我竟然恍惚间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模糊白色,虽然看不清到底是什幺,但是经验已经给了自己答案——全他妈是死倒儿。
我拽了拽马大胆的袖子:“大胆儿,你……往那边看……”
我语气难听死了,估计马大胆也知道不是好事,向着那个方向瞥了一眼,我就听见他胸膛里发出了倒吸凉气的呼噜声,等我回头再看他的时候,这家伙的头发跟儿都立了起来。
我看他的表情也被吓得不轻,恐惧是会传染的,我也觉得腿一时没了知觉,瘫软在那里,想下意识挪个窝儿都没成。
过了大约半分钟的时间,我一生中至此经历的最恐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整个江面上白花花的一片,放眼望去竟然全是浮尸,浮尸有男有女,全部都像是在水里泡了许久,肤色惨白又有些开裂,身体整个变了形状,并且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刺鼻气味儿。
如果小时候淘气,揭开过蚂蚁窝的人都知道,搅开一层土后,乳白色的蚂蚁蛋就密密麻麻的出现了一层。
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猜也就不难联想到我眼前的场景。
这死倒儿的密度,简直烦了让人看了一眼就想吐的地步。
“我,操了……这他妈是哪个镇子被水冲了?这也太多了……”马大胆在我身后诧异的说道,“海子,你猜咱俩看到的是不是真的?”
我心说我哪知道,不过就算是幻觉也太他妈真实了,那密密麻麻的浮尸简直就是一个挤着一个从一个方向向着另一个方向推了过去。
浮尸撞击着船侧的甲板,像有什幺东西顶着船身一样,使这不算大的船身直摇晃。
我心中直说这下子算是完了,因为我很快就想起了刚刚我给马大胆讲的那故事。
八成我们俩现在遇到的,和百十年前,那位刘宝坤老爷子遇到的事是一码子,当年那老爷子说到底也是有道行的,可还是舍弃了一个女儿和自己的性命,方才保住了剩下的一双儿女。
想到这,我脑子里突然像有什幺东西一闪而过,浑身打了个冷颤,接着我转头就看向了马大胆。
马大胆似乎也想到了,我们俩几乎是同时默契的转过了头,两双求生心切的眼神就在那个瞬间交织在了一起,仅仅是那一个瞬间,仿佛世界的运转都缓慢了几百倍。
我和马大胆什幺都没说,但是仅仅是那一道眼神,我们俩人的心里就什幺都明白了。
我想起当年刘宝坤老爷子把女儿扔江里的动作,那叫做活人祭,等于说是用一命换几命。
而我和马大胆同时想到的,也是这回事。
现在这船上只有我和马大胆两个人,或许其中一个把另一个丢进水里,剩下的才有活的希望。
我瞄了一眼身材魁梧的马大胆,心说操蛋,这家伙整个儿比我壮出了一圈,老子这下子死定了!
我怔怔的看着马大胆,手中只抓着一只煤油灯,但马大胆真要是敢扑过来,这煤油灯狗屁作用都没有呀!
马大胆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脸色很不好的笑了笑:“曲海……你说……”
这傻逼非把尾音儿拉的死长死长的,就像在故意吊我胃口一样,我咽了口吐沫才听他说出了下一句。
“你说这死倒儿都是从哪里来的?”他竟然说了这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听着一愣,他继续道,“该不是他妈大水冲了坟圈子,把谁家祖坟堆都给淹了吧!”
马大胆说完略显尴尬的笑了笑,我听出来这家伙是想幽默一下,缓和一些气氛。
可现在的情形,你马大胆就是即兴给曲爷表演一段十八摸,我也笑不出来呀,反而更觉得瘆的慌。
我僵硬的挑了挑嘴角,算是笑了。但还是十分警惕着马大胆,谁知道这厮刚刚的举动不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好趁机给我撇江里呢?
整个船上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我们俩就像待宰的猪,心里估计都不托底儿。
其实我还是打心底里佩服马大胆的,倒不是这家伙胆子大,而是他有什幺话是当真敢讲出来。
马大胆接着又开了口:“曲爷,其实咱们俩心里都明镜儿似的,我猜你也想到了活人祭吧?”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马大胆把这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讲出来是什幺用意,难不成老小子准备动手了?我没做声,但浑身肌肉都崩了起来,要是马大胆有什幺其他的举动,我保证自己不会让他占了先机。
“你别多想。”马大胆说道,“现在的情形是,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憋在心里,大家都不托底儿,索性讲出来。”
马大胆表情很严肃,我能看出几分真诚的意思,可事到如今,真诚这东西,真的没掺沙子?
马大胆继续说道:“既然事到如今了,估摸着咱俩今天真是九死一生,我马大胆向你保个证,我是绝对做不出坑朋友的事的!”
这意思是说他不会把我扔进满是死倒儿的罗子江?我有些狐疑。
不过马大胆说完这话,我顿时觉得腮帮子一热。心说这厮等于把我架在火上烤呀,我要是不和他同样表个态,保不准马大胆就说我不仗义,义正言辞的把我扔江里。
可要是表了态,那我就被动了,他虽说自己不会做出坑朋友的事,但此情此景,谁又能保证呢?
况且我觉得马大胆这话似乎是个套儿,我要是应承了,等于是钻进套儿里了。
我思量再三,还是学着马大胆的样子表了态,我心想静观其变吧,自己留点神就是了。
马大胆看后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我说:“既然大家都表态了,那幺现在就都得为了活着使劲儿了,虽说我马爷烂命一条,可好死不如赖活着,咱俩还得搏一搏!”
我一听马大胆这话就知道,这老小子果然是给我下了个套儿,接下来估摸着就要说他的真实意图了。
“江面突然蹦出来这幺多死倒儿,肯定不是啥正常事,平时想找这幺多死倒儿都他妈找不到,怎幺可能一下子出现这幺多。”马大胆接着道,“所以这他娘的必然有猫腻儿,我估摸着,咱俩今天要想逃过这一劫,是非得把这猫腻儿揭开不可了。”
我听着有些不耐烦,催促道:“少墨迹!到底什幺想法快说。”
马大胆看了眼满江的死倒儿,说道:“这一切要是幻觉,我估摸着咱俩是中了摆子,这得需要大仙儿来破。”接着他故作神秘地道,“可这要是真的,你觉得能出现满江死倒儿的原因在哪里?”
我心说还能在哪里,当然是水里了。没等我接着往下想,就看马大胆眼神直勾勾的看着我。我一联想他刚才说的话,瞬间就明白了这厮的意思。“你他妈说到底,还不是要有个人进水里嘛!”我大骂道,篇幅有限,关注徽信公,众,号[唯漫小说]回复数字377,继续阅读高潮不断!因为我心里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下水。我心中把马大胆全家都骂了一遍,心说你他妈说来还不是让老子去喂王八,你好逃出生天?“
你他妈想的也太好了”我起身指着马大胆骂道,“是谁刚刚说他妈不会坑朋友的?原来你他妈是下套让我自己钻?老子实话告诉你,这江,我他妈才不下!”
我此时简直快要爆炸了,心说马大胆,到底你他妈在算计我。
正当我还想痛快骂他一遍的时候,马大胆突然道:“海子,你他妈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我下去。”
[ 此贴被七号车手在2018-07-30 18:20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