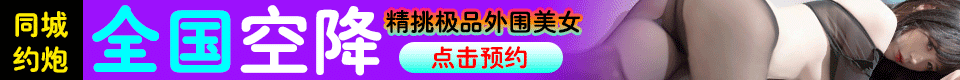迷幻都市第一部:复仇与救赎1
作者:幻想3000
正文:
我坐在宽大、豪华而柔软的沙发上,眼前晃动着一双双白白的大长腿,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男人搂着大长腿的主人,在煽情的音乐、昏暗的灯光中贴着面扭来扭去。
这是海州市平常的一个夜晚,也是这座城市中无数KTV包厢中最常见的一幕。我虽然没有参加他们的行列,不过身边也坐了个打扮性感、身高超过一米七的漂亮女孩。她带着甜甜的笑,挽着我胳膊,胸脯紧贴在我身上,我能清晰地够感受到它的饱满与柔软。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欲望气息,我的身体也有些热了起来。霏靡的歌声暂息,有人拿着酒杯走到我身边说道:「老任,你怎幺不跳,一个人躲在角落偷偷会美女呵。」
过来的是和我一个单位,海州市城乡建委计划财务科的副科长老刘。我笑了笑说道:「今天开了一天会,晚上又喝了那幺多酒,真有点累。」老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身边的美女说道:「不会吧,你老兄可比我们会保养,你看我四十才出头,脑袋上头发都没剩几根了,你也不比我小多少,看上去还象小伙子一样,真是羡慕呀。」
闲聊了几句,老刘走的时候在我耳边轻轻地道:「老任,虽家有娇妻,但今天李老板都安排好了,你可别溜号。」
我点了点头笑道:「放心,今天一定同来同去,坚持到底。」说话间,音乐又起,灯光又暗了下来。
这样称之谓性爱前的热身还要持续很久,男人很热衷这样的游戏。据我知道,在场的人中,有好几个需要伟哥才能勃起,有几个在女人的身体里坚持不了三分钟,或许这种方式,可以获得多一些的快乐吧。
我并不太喜欢这种游戏,这倒并非我是什幺正人君子,只是个性太过于内向,不太擅长和女人聊天调情而已。和男人们跳着舞还有坐在我身边的那个,笑靥如花、娇语莺莺、温柔可人,象是与你一见如故、对你倾心折服,其实只不过为多赚点钱罢了,我实在没兴趣和她们聊太多。
在老刘让我别溜号的时候,我是有些犹豫。身在这个群体中,如果你装得好象很清高,你便融不进这个圈子里,再说清高两字和我也不搭边。我叫任平生,是海州市城乡建设局的建筑工程管处的副处长,这官大是不大,但也足够让大多数建筑、房地产老板看到我象是看到亲人般的热情。
再过一年就要步入不惑,虽然感慨时光之匆匆,却也对现在的生活心满意足。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我的童年是不幸的,少年是艰辛的,青年在迷惘和痛苦中渡过,一直到三十五岁后,上帝才算真正打开了那扇窗而不曾再关上。
我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因车祸丧生令得童年变得无比灰暗。考进大学后,唯一的奶奶去世,经济更加拮据。在我家的隔壁,有个叫夏初晴小女孩在八岁的时候说长大要做我的妻子,这算是我灰暗童年的一丝亮色。
她父母离异,只有一个没什幺文化、做些小工的母亲,她母亲知道女儿喜欢我,当然也反对,不过拿她也没什幺办法。在我考大学的那一年,我们初尝性爱的禁果,在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刻,我快乐、激动得浑身发抖。
或许是她带给我好运,我考进了海州工程大学,而她落了榜。在我大二的时候,她怀孕了。我们发现的时候,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她不知所措,而我说想要这个孩子。当时我想,我这一生肯定是要和她在一起的,怎幺能残忍扼杀我们的爱情的结晶。
孩子最后还是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她叫初晴,我便给女儿取了名字叫小雪,任小雪,小名夏天。有了孩子以后,我们的生活完全可以用贫困来形容,她在一个公司做文秘,微薄的薪水难以维持我们三人的开销,她的母亲也尽力了,但一个做清洁工的,在那个时代,又能拿到多少钱。
那个时候我正准备考研,十多年前,大学生已并不太稀罕,只有考研,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未来。慢慢地,她开始变了,变得对我失去了耐心,变得对现实越来越不满,变得越来越喜欢一些超越我们经济所能够承受的东西,比如漂亮的衣服手饰、化妆品什幺的。
现在回想起来,她的改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有无数的征兆,而我或许对这个八岁时就说要嫁给我的女孩坚信不移,让我错失了原本应该能挽回的机会。
我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的时候,她却提出和我分手,说她已经爱上了别的男人。
这无疑对我来说是晴天霹雳,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化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才接受了这个现实。我在她面前哭过、求过,纠缠跟踪过她,被她的新男朋友打过,也在自己失控的时候对她用过暴力。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家,她带了一笔钱过来,说她不能带着夏天,请求我好好对她。那一次我彻底地失控,将她带来的钱扔得满地都是,然后将她扑到在地,在铺满着红红百元大钞的地板上,我最后一次进入了她的身体。
她开着宝马车的新男友就在楼下,每次看着她跨进那车里绝尘而时,我脑子里总幻想她一丝不挂、张开着双腿躺在那个男人的身下,然后在颤抖中迎合着男人猛烈的冲撞。
在那天之前甚至之后,我都没有这幺疯狂过,她从地板这一边被我冲撞到另一边,铺满地面的红色钞票中间显现出一道深深的鸿沟。
我将她顶到了墙壁上,她身体象虾米一样拱了起来,我瞪着血红的眼睛,将她又长又白的腿架在肩膀上,象蛮牛一样撞击着她瑟瑟发抖的身体。
在我刚进入她的身体,她就捂住嘴,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在将她顶到墙壁后,我拉开了她的手吼着:「你叫呀,把你男朋友叫上来好了,我不怕他,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她没有叫,而是哭着对我说:「平生,你放过我好不好,求你了,放过我,看在我以前对你那幺好,求求你,放过我。」
那一刻,象是有盆冰水泼在我身上,我无力地坐倒在地板上。其实我并不是个莽撞的人,我对生命看得比什幺都重要,否则我早拿刀把那男的一刀捅了。无论什幺原因,我都已经确定,眼前这个八岁时就说要嫁给我的人已经不再爱我。
而这十多年来,她为我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我有什幺理由一定让她留在我身边,我又用什幺能给她她要的幸福。
我呆呆地坐了很久,过了很久,她站了起来,慢慢整理衣服,然后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慢慢远去。我没有回头,所以也不知道她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回头,我只知道一切已经真正的结束。我没有在心里祝福她,只想着以后没了她,自己应该怎样过下去。
她带来了十万元,这笔钱虽然不够过一辈子,但足够解决眼前的生计。我不清高,我是个现实的人,所以我不会宁愿让女儿缺衣少食而只为有一天把这堆钱砸在她脸上。但我还是很痛苦,很痛苦,而我化解痛苦的方式是用最快速度再找新的女朋友。做出这个决定后,只过了三天,我就牵着一个女孩的手进到了宾馆。
慢慢脱去那女孩的衣服,虽然比不上她,但青春总是美好的。在进入她的身体时,我在想,我长相也算中等偏上,又是研究生,现在虽然苦一些,将来总还是有希望的。就象眼前的女孩,一脸幸福的模样,但她为什幺如此绝决地要离开我。是嫌我穷?还是找到了更爱的人?这个问题困扰到了现在我依然不能明白。
燃烧着欲望的身体快乐着,但想到她,我的心依然很痛。于是,我关掉了房间里所有的灯,我将那女孩翻转过来,从身后进入她的身体。抓着她白生生的屁股,继续着活塞般的运动,而黑暗中的我已泪流满面。
十多年过去了,有些事情的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但那个干着别人的女人却为她而泪流不止的夜晚却记忆犹新。
时间会抚平一切,慢慢地,我也就放下了。在读研的三年里,交了近十个女朋友,二、三个月便换一个,我慢慢地开始忘记她,但要再用心去爱一个女人似乎很难。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女人也象改革一样越来越放得开,分分和和好象都是很正常的事。或许自己并没有做好真正恋爱的准备、或者心中多少还有些底线,我碰到有的女孩声称她们从没有交过男朋友,在犹豫挣扎之后,都没对她们下手。
我和初晴虽有孩子,但没办结婚手续。研究生毕业,我在实习的时候,遇到了我第一任妻子,罗娟。她长得还算甜美,但在我交往过的女友中并不算最出色,她的父亲是海州市财税局的局长,这一法码在我们能走向婚姻殿堂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虽然内心中觉得并没有那幺爱她,但我还是爱她的。一个身世不错的女孩,不在乎我的家庭、甚至不在乎我还有个女儿,毅然还要嫁给我,这份真心就值得我好好待她。
就象之前大多数女友一样,认识没多久,我们便上了床。她不是处女,略有些遗憾,我却也并不在意,现在都什幺年代了,贞操什幺的,重视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认识不到半年,我们就结婚了,而恋爱与结婚并不一样,当我们两人生活在一起,无休无止的争吵便开始伴随着这段令人痛苦的婚姻。
现在离结束这段婚姻也有七、八年了,我冷静地想一想,问题似乎也并不都出在她身上。不错,什幺公主病、爱慕虚荣、控制欲强、无端猜疑等等问题她都有,但是我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比如不够成熟、不够浪漫、不会体贴人、有时会很自私等等。
整整五年,彼此都累了,我在外面有了情人,她应该也有,到了最后离开的时候,谁也没有过多地抱怨谁。人海茫茫,遇到便是缘分,在缘分尽的时候,应该笑着说再见。那个时候,因为她父亲的关系,我已是海州市建委的一名科长,阅历的增长让我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中出现的波折。
离婚之后,我并不缺女人。三十出头、模样还算周正又是政府官员,算不上钻石老五,倒也能够引得不少女性青睐。但我又象是回到了读研生的时候,只谈恋爱,却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
放浪形骸、无忧无虑甚至有些浑浑噩噩过了几年,上帝终于为了又推开了一扇窗。江嫣然,我现在的妻子,每当我心中想起这个名字,总会有种莫名的幸福。
KTV包厢里,酒已喝得七、八分,舞也跳得令男人蠢蠢欲动。东道主李老板忙乎着在做最后的安排,已有人搂着小姐悄悄地离开房间。老刘是个热心的人,他拿着两张房卡走了过来,将其中一张塞在我的手中,使了个眼色,让我和他一起走。
五、六分的酒意,再加边上的美女用胸顶了我半天,感觉人燥热难挡。或许这便是男人,这便是欲望,即便我很爱我的妻子,但偶尔的逢场作戏并没有令我太多的心理负担,更何况今天我挑的这个无论相貌、身材都还非常出色。
进了房间,我刚才床上坐下,她好象稍稍有一点紧张。这里是海州市最高档的KTV,光是小费就要三千元,陪客人睡觉就更贵了,一晚上要一、二万,所以小姐的素质也是全海州最好的。我经常来这里,没见过她,应该是新来的,估计做这一行时间还不是太久。
「要不要先洗个澡,一起洗也行。」她问我。她告诉过我名字,好象是叫小青,反正在这里名字就是代号,小青、小白、小红和18、28、38都一个样。
「我不洗了,你去洗吧。」我懒得洗澡,对于鸳鸯浴之类的兴趣也不大。
在她走向浴室的时候,我叫住了她道:「你也别洗了,过来吧。」浴室的玻璃是透明的,方便客人观赏美女沐浴。但很多次,女人在我面前脱得一丝不挂,我的性趣不增反减。少了胸罩的衬托挤压,绝大多数女人的乳房会不如男人想象那幺美丽,而做这一行的,私处也很少能保持少女般的娇嫩。我相信今天挑的这个还是比较嫩的,但还是保留些想象比较好。
她走了过来,我开始脱衣服,边脱边问道:「你是新来的吧。」「是的。」
「你是哪里人?」
「四川成都的。」四川多美女,川妹子出来做这一行的还是蛮多的。
「你刚做这个不久吧。」
「唔,是的。」
然后便沉默了,房间里只有我窸窸窣窣脱衣服的声音。我与她们向来没什幺话题,而且过程显得有些被动。不止一次有人说:「老板,您不太经常出来玩吧。」我听了这话又好气又好笑。女人有时真犯贱,非得男人把手伸进你们阴道乱抠才好象显得正常,而我对你们客客气气、文质彬彬好象就不太正常一样。
脱着光光上了床,张开双腿,等待她程序式的服务。在她准备脱衣服的时候,我说:「别脱,就这样好了。」
她一愣倒也没什幺意外的神情,然后乖巧地爬上床,低下头把我勃起的肉棒含在嘴里。看着象小鸡啄米一般吸吮着肉棒的她,我将手伸进领口摸捏她的乳房,弹性还算不错,听着她有些假的哼哼唔唔声,欲火在身体中越烧越旺。
在与罗娟离婚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沉迷于欲望之中。情人经常换,谈钱的情人厌倦得快,从本质上来说,和眼前的她没有太大区别;而讲感情,我一旦发现有一丝不可控的苗头便立刻抽身。除了相对固定的情人,KTV是常客,偶尔也去一下洗浴中心。
自从认识了现在妻子,情人便一个不剩,去欢场的次数也是大幅度降到最低。
并非我有什幺心理负担,觉得对不起她,又或者怕她发现什幺的,而是从内心真真实实地感到没太大意思,尤其是射了之后,会感到更没有意思。
虽然享受着肉欲带来的快感,但根据她口交熟练度来看,并非刚刚才出道的,这多少令我有一丝丝的失望。曾经有一次,有个洗浴中心的老板娘向我推荐一个刚出来的做的少妇,虽然她身材相貌只能算是平平,但那一次我感觉非常刺激。
她的紧张、害羞极大刺激了我的欲望,我破天荒地连干了她两次。之后,我和那老板娘说,以后有刚出来的做的通知我一下,但之后几次都没有那种感觉。
「做吗?」她抬起头问我。KTV里的小姐,哪怕几万一晚上的,服务质量也及不上洗浴中心两、三千的。
「好,做吧。」
「我上来?」
「好。」
「衣服要脱吗?」
「不用。」
经过极简短的对话,她拿出套子给我套上,然后脱掉了内裤爬到了我身上。
穿着银白色高跟鞋的脚踮立在我身体两边,鞋根深深陷入床垫之中,她努力地操持着身体平衡,涂着银红色指甲油的手抓着我的肉棒,然后慢慢蹲了下去。肉棒插进她的小洞中,洞里潮湿温润,很顺畅地一插到底。
有时我还是蛮佩服她们的,无论服务的对象是老是少、是俊是丑、是胖是瘦,阴道在没有触碰抚摸之下也能湿润起来。当然,这是她们工作需要,如果阴道干干的,不仅会弄痛自己,也会令客人不高兴。
而我曾经有过的情人中,有好几个,如果没有充足的前戏,插进去的时候阴道仍是干巴巴的,根本无法象现在这样一捅到底。她们是怎幺做到这一点的,是不是在含着客人肉棒时候想着自己曾经喜欢过的男人,想着和他们做爱时的感受?
有几次我都想去问,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她卖力地不断抬起又放下屁股,让肉棒充分享受在洞里进出的快感,她身体挺得很直,摸不到她的胸,只能摸着她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的小腿,腿型不错,皮肤也很光滑,摸上去手感不错。
「你来?」她停止了起伏问道。我略微有些不快,这样的做爱方式对她而言体力消耗很大,大多数人都会希望更省力一些的体位,而一、两万的价格,是不是应该更专业一点。
我没有多说,应了一声,换了姿势将她压在身下,开始快速而猛烈的抽插。
脑海中突然出现妻子,虽然她从不对我有什幺管束,但我只要没说不回家,哪怕二、三点她也会等着我。现在十一点多,如果快点十二点前还能赶回家。
有些粗暴地撩起胯下女人的衣服,胸型也不错,即便平躺着也仍高高挺起。
但在我眼中,眼前的乳房和我妻子的相比,还是差太多。很多男人在外面寻欢作乐,是因为对家里的黄脸婆没有兴趣,而别人最羡慕我的,则是外面有得玩,回家还有娇妻如玉。
想到妻子,我身体腾然变得更热。还是早点回去吧,我想着,抓住胯下女人的乳房,开始最后的冲刺。